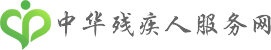山東4殘疾人組成樂器樂隊,合練僅一月贏得全國一等獎
| 2017年8月18日 | 分享到: | 來源: |

一段簡單的序曲結束,嗩吶、二胡、板胡、墜胡齊響,歡樂的聲音在大劇院里回蕩。8月16日下午,在濟南省會大劇院,當四位殘疾人再次奏響這曲改編后的《洞房花燭》時,整個劇場都被他們打動了。這四個人分別叫高全明、翟春華、魏雅然和王文堯,但從這歡快的音樂中聽不出,他們中有兩個是盲人,一個弱視、還有一個是肢體殘疾。這是第九屆全國殘疾人藝術匯演的匯報演出,就在幾天前,這個四人組合憑借這一曲《洞房花燭》獲得了第九屆全國殘疾人藝術匯演東部片區器樂組一等獎。
拉琴30多年,獲獎有些意外
16日下午,在省會大劇院后臺等待著上場演出,戴著墨鏡的高全明看上去十分淡定,自從10歲學習墜胡,到今年已經整整32年了,從來都是在老家高唐街頭巷尾賣藝的他,從沒想過會登上這么大的舞臺,靜靜地聽著前臺已經開始的演出,高全明也沉浸在舞臺音樂中。

“小時候父母送去學藝,無非是為了學門手藝,好討口飯吃,自己雖也熱愛這個行當,但能登上舞臺其實是個意外。”高全明依舊習慣說自己是個街頭藝人,盡管這兩年參加了幾個比賽,拿了幾個金獎,但在比賽之后,他依舊會回歸街頭。“習慣活躍在老百姓之中了。”高全明說。
在這個《洞房花燭》的合奏中,高全明的角色其實是新娘的父親,要將女兒出嫁的歡喜與憂傷都在墜胡里表現出來,對老高來說,這些都游刃有余。“這些年,習慣了在街頭一個人表演,邊彈邊唱,西河大鼓、山東琴書、河南墜子、山東呂劇……都十分拿手了。”高全明說,雖是盲人,但他感覺自己在音樂上的努力并不差于一般的專業演員。“小時候跟師傅學琴,讓你三九天在屋外拉,必須要練到手沒知覺了也能把音拉準才能進屋。”
從沒進過專業的劇團,但高全明總會沉浸在自己的演奏中,“雖然看不見這個世界、見不到光,但音樂就算是我的光吧,可以用它和任何人交流。”高全明說。
雖是民間藝人,但視音樂如知己
在這個名叫“嗩吶與三胡”的演出中,來自濟寧魚臺的翟春華就是那個嗩吶,與高全明一樣帶著墨鏡,感觸不到一絲光亮,但也如高全明一樣視音樂如知己。“他們都叫我小孩。”說起話來就如同他在演奏中新郎的角色,帶著一些幽默。學吹嗩吶15年了,這個30歲的小伙子如今也是兩個孩子的爸爸。被稱作隊伍里的“大牌”,只是別人不知道,這個大牌的嗩吶基本上是自己從錄音機里自學的。
“上了兩次嗩吶學校,一共上了差不多40天,以后就都是自己學了。”翟春華說,學吹嗩吶的那年是2002年,他已經15歲了,自學了一年,就加入了一個嗩吶班,于是在老家魚臺的紅白喜事上,便時常能見到這個帶著墨鏡的小伙子盡情地吹著嗩吶。“這不僅僅是一個謀生的技能,確實是特別喜歡音樂,音樂就是一個知己,看不到譜子,都是自己一句一句跟著錄音機學,要不是真的喜歡,可能就堅持不下來了。”翟春華與樂隊里的扮演新郎父親角色的老鄉王文堯一起練習著演奏,倆人十分默契。在今年6月份的全省殘疾人藝術匯演中,翟春華得了金獎,右腿有些殘疾的王文堯得了銅獎。
“都算是民間藝人吧,算不得專業,但大家都把手里的樂器當做生活里不能缺的伙伴了。”王文堯演奏的是板胡,為了適應《洞房花燭》這個由嗩吶曲改編的音樂,已經66歲的他也是拼了老命,“老母親有病,本來不想來了,但缺了一個人,大家就都沒法演出了,畢竟能上一次大舞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”從合練到比賽的時間只有一個月,為了記譜,老王用了10天的時間,“十幾頁的譜子,沒想到能背下來,但為了演出效果,還是把譜架子給避免了。”
最年輕女隊友,已是民大大學生
在這個四人團隊里,魏雅然是唯一的女生,兩只眼睛的視力分別只有0.1和0.06,但化好妝、身著彩裙的她依然光彩照人,她便是四人合奏中的那個新娘了。同樣是因今年六月份的比賽結緣,與其他幾個純粹的民間藝人不一樣,魏雅然已是中央民族大學二胡表演專業的一名大三學生。

與化妝室里其他的小姑娘相互鼓勵著,魏雅然總是一臉燦爛,只是視力不好,媽媽總要陪在左右。“從五歲開始查出眼睛有問題視力開始逐漸下降,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學音樂了,我對音樂是真的喜歡。”演出開始,魏雅然悠揚的二胡聲時透出新婚的喜悅,偶爾也流露出一絲離開父母的憂傷,伴隨著音樂的起起落落,魏雅然的喜悅表情里也不斷有著微妙的變化。“當年參加高考,雅然是以專業第二名的成績考上的中央民族大學。”媽媽很為這個女兒自豪。當年讀高中,雅然看不清試卷和書本,都是媽媽幫她讀著學習,看不清樂譜,爸爸專門給她抄大號的。
“因為看不清樂譜,沒法合練,以后畢業了很難進入一個樂團工作,但我享受拉起二胡的每一刻。”魏雅然說,與三位哥哥、叔叔的合奏贏得了一等獎,也給她一個很大的鼓舞,“身有殘疾并不是個什么障礙,只要是好聽的音樂總能打動人。”
文章來源齊魯壹點